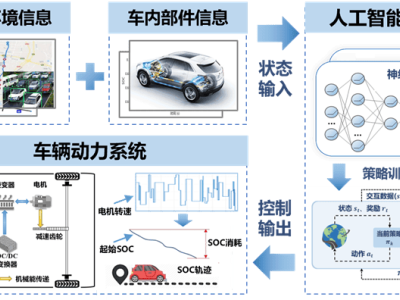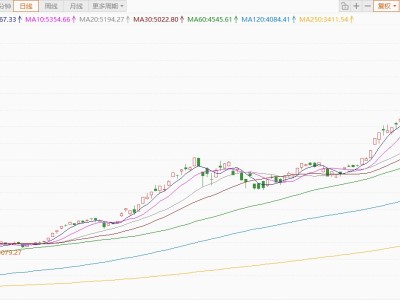歲末寒冬,我又一次踏上歸鄉的旅途。窗外的風景從高樓林立慢慢退成連綿的田野,車廂里人聲漸雜,年味漸濃。
我今年四十有七,在外奔波半生,見過起落浮沉,嘗過冷暖人情,本以為早已練就一副不動聲色的心腸,可越是靠近故鄉,心越是不由自主地軟下來。
只是這柔軟里,永遠帶著一道淺淺的、化不開的缺口。
2012年5月,母親因病永遠離開了我。一晃,已是十四個春秋。
車子緩緩駛進村口,第一眼看見的,還是那棵老槐樹。
樹干粗壯蒼勁,枝椏向天空舒展,像一位守了一輩子歲月的老人,沉默、穩重,又帶著說不盡的溫柔。
小時候,我總在槐樹下瘋跑、打鬧、和伙伴們捉迷藏,母親就坐在樹下的小板凳上擇菜、縫補、納鞋底,時不時抬頭喊我一句:“慢點兒,別摔著。”
槐花盛開的季節,滿樹雪白,風一吹,甜香飄滿整條巷子。母親會拾起干凈的槐花,蒸成槐花飯,清清淡淡,帶著一絲甜,那是我童年最安心的味道。
如今樹依舊,葉仍青,只是樹下那個時時牽掛我的人,再也不會坐在那里等我了。
站在老槐樹下,陽光透過枝葉灑在身上,暖得有些刺眼,也涼得心口發疼。這棵樹,見證了我的出生、我的成長、我的遠走,也默默送走了我的母親。
母親一生平凡,沒讀過多少書,一輩子圍著灶臺、家庭、田地轉。她不懂什么大道理,卻把最深最細的愛,全都熬進了一瓶瓶西紅柿醬里。
每到盛夏,西紅柿最便宜、最紅透、最沙甜的時候,母親總會提著竹籃去集市,蹲在菜攤前仔細挑選,一挑就是一大筐。回來后,洗凈、燙皮、去蒂、切碎,然后守在灶臺前,小火慢熬。
她從不多放調料,只靠耐心和火候,把西紅柿熬成濃稠鮮亮的醬。熬好后,趁熱裝進洗凈晾干的玻璃瓶里,密封嚴實,放在陰涼處存好。那一瓶瓶紅彤彤的西紅柿醬,是我從小到大,最踏實、最熟悉的鄉愁。
無論我多晚回家,母親總能從柜子里摸出一瓶西紅柿醬。
煮一碗清湯面,舀上一勺,熱油一潑,“滋啦”一聲,香氣瞬間溢滿屋子;炒雞蛋、燉豆腐、拌米飯,只要有它,再簡單的飯菜,都變得有滋有味。
在外求學、工作的那些年,每次離家,母親必定往我包里塞好幾瓶。她說:“外面吃不到家里的味道,想家了就開一瓶,暖暖胃。”
那時的我,偶爾還會嫌重、嫌占地方,如今回想起來,才真正明白:那一瓶瓶沉甸甸的,哪里是醬,分明是母親裝也裝不下的牽掛。
母親走后,家里再也沒有人熬西紅柿醬了。
這些年,我也試著自己做過。選最好的西紅柿,按記憶里的步驟,洗凈、去皮、切碎、慢熬,可無論怎么努力,味道總是不對。
少了她在灶臺前忙碌的身影,少了她一邊攪鍋一邊念叨我的細碎話語,少了她看我吃得香時滿足的眼神,再精準的配方,也熬不出當年的溫度。
我終于明白:好吃的從來不是西紅柿醬,是做醬的人,是那份不求回報、默默守候的愛。
十四年,故鄉的模樣一年比一年新。
曾經坑洼不平的土路,早已修成寬敞平整的水泥路;村口的老小賣部換上了新招牌,裝上了掃碼支付,不用再揣著零錢來回找補;鎮上開了新超市,果蔬生鮮一應俱全,快遞也能直接送到家門口。
鄉親們的日子,一天天紅火起來,樓房多了,車子多了,笑容也多了。
鄉村在發展,時代在向前,一切都在變好。
只是有些東西,再也回不來了。
父親依舊守著老屋,身體還算硬朗。他不常把思念掛在嘴邊,卻把與母親有關的一切,都好好留著:母親用過的灶臺、縫補的針線、裝西紅柿醬的舊玻璃瓶,甚至是院里她親手栽下的幾株花草。
每次做飯,父親總會下意識多擺一雙筷子;
每次路過老槐樹,都會默默站一會兒;
每次收拾柜子,都會把那些舊瓶子輕輕擦一遍。
有些思念,不必說出口,早已刻進日復一日的煙火生活里。
今年歸鄉,我特意翻出了母親當年裝醬的舊玻璃瓶。
瓶子被父親洗得干干凈凈,收在櫥柜最深處,瓶壁上還留著淡淡的紅色印記,像時光不肯抹去的痕跡。
我捧著瓶子,站在曾經母親忙碌的灶臺前,恍惚間,仿佛又看見她圍著舊圍裙,站在鍋邊,小火慢熬,陽光落在她的發梢,溫柔得讓人心頭發酸。
人到中年,才真正讀懂“子欲養而親不待”這句話有多痛。
年輕時總以為來日方長,總覺得還有很多時間,總想著等事業穩定了、等生活寬裕了、等有空了,再好好陪母親,好好帶她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可我們都忘了,歲月從不等人,生命也從不會給我們預留足夠多的“以后”。
我還沒來得及好好跟她說一句謝謝,
還沒來得及讓她真正享幾天清福,
還沒來得及讓她看看我如今的模樣,
她就匆匆轉身,留給我一生的念想與遺憾。
年夜飯的桌上,我和父親相對而坐。
少了往日的熱鬧,卻多了幾分沉靜的溫情。
我學著母親的樣子,洗菜、做飯、端菜上桌,菜色簡單,卻滿是心意。飯間,父親和我說起村里的變化:誰家承包了果園,誰家孩子在外打拼有了出息,村口的荒地改成了小廣場,鄉親們晚飯后也能跳跳廣場舞、散散步。
我靜靜聽著,心里既欣慰,又悵然。
這一切越來越好的光景,母親再也沒能親眼看見。
臨行那天,天剛蒙蒙亮,父親就起來了。
他往我車里塞了滿滿一車東西:自家種的青菜、蘿卜、曬干的豆角、新蒸的饅頭,一層又一層,擺得整整齊齊。
他沒有找到母親做的西紅柿醬,只是反復叮囑:
“路上慢點,照顧好自己。”
“別太累,注意身體。”
我點點頭,不敢多說話,怕一開口,眼淚就掉下來。
車子緩緩駛離村莊,老槐樹的身影漸漸變小,最終消失在視線里。風從車窗吹進來,我好像又聞到了槐花的甜香,聞到了灶臺邊西紅柿醬的酸甜,聞到了童年里最安心的味道。
十四年生死,歲月匆匆,母親從未真正離開。
她化作村口的風,化作院里的樹,化作我味蕾深處最熟悉的味道,永遠留在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上。
四十七載人生,半生風雨,半生滄桑。
如今我終于明白:
歸鄉,從來不是為了一場熱鬧的團圓,而是為了尋根;
懷念,也不是為了沉溺悲傷,而是為了帶著愛繼續前行。
老槐樹依舊,
西紅柿醬香藏在心底,
母親的愛,從未走遠。
往后余生,
我會好好照顧父親,好好生活,
帶著母親的期盼,穩穩地走下去。
不負歲月,不負故土,不負那份,從未斷過的親情。
這,便是我這一趟歸鄉,最沉、也最暖的心事。